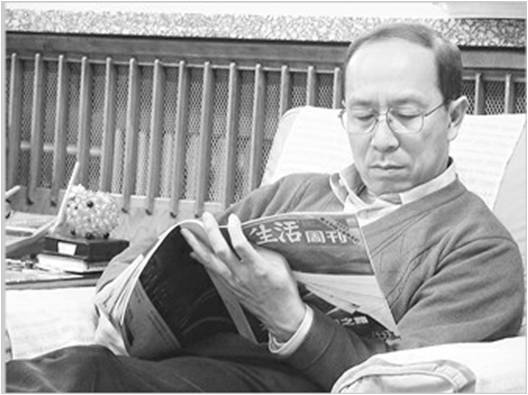|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 |
|
登录日期:2010-09-06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文汇报》2010年9月6日第8版 |
| 金一南的“苦难”与“辉煌” |
|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阅读次数:21831
|
题记 借最近一次去上海讲学的机会,金一南看了世博会。德国馆内4枚不起眼的小铜牌震动了他。 “上面分别刻写着哪个楼的哪个房间住了哪几个犹太人,他们的姓名、生卒,谁逃走了,谁被枪毙了,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在德国,有人专门搜集这类信息,做成一块块小铜牌,嵌在楼外的石板路上,你走到那里,就能看见。这是无言的反省,是正视历史的真诚,他们强调的,是历史的记忆。” 那么,我们呢? “我们有些人却生怕自己记住东西!”这位国防大学的战略研究专家从近忧之中看到了远虑,“有一种声音,嚷嚷着淡忘耻辱、淡忘苦难、淡忘悲情、淡忘背叛。这些好像成了历史的包袱,扔掉才能轻装前进。但他们不知道,同时被扔掉的,还有苦难酿成的坚忍、激情、力量、光辉。美国历史二百年,他们在不断挖掘;华夏文明五千年,我们有些人却在不断否定。人一旦浅薄,危及的将是民族根基。” 不知来路、不懂牺牲,又怎能看清方向、崇尚大义? 在被荒弃、风干的历史面前,人们心无所依,心无所悟,心无所敬。 仅拿1921年至1937年我党我军的早期历史来说,那个浴火重生的热血时代又能在今天点燃多少人的激情?“历史,一段紧接着一段,好像是满的,但我看到了空白。”金一南所著的《苦难辉煌》没有采用阐述历史的老方法(比如把那段历史概括为路线斗争史、统一战线史、个人英雄史),而是在把握各方面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俯瞰,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力量交锋中,用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华民族一大批救亡图存者在重大关头面前的命运。让他们的胆略、抉择,流血、牺牲,主义、信仰,穿透重重历史迷雾,鲜活地走进时代的镜头。 这样的历史,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力量之源的回溯,是自身使命的重提,是队伍建设的自省;对年轻人来说,是激情的传递,是隔膜的消融,是对个人命运以及党和国家前途的自信。《苦难辉煌》被中宣部、中组部联合列为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同时又在民间口口相传,自去年1月出版以来已是第十六次印刷,总印数突破30万册。 关于《苦难辉煌》的解读,成了这一年多来诸多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但我本意不在对书籍本身加炭添薪,而是试图退到此书的光环之外,去关注作者本人苦乐交融的心路历程,正是这一历程塑造了他独特的历史观,历史观又成为他开掘历史富矿的最有力武器。 历史在《苦难辉煌》中再现并昭示今人,是我们的幸运;用正确的历史观留下包括今天在内的人类历史并昭示后人,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的前言里说:“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他用“地火”比喻隐含在历史事件中的、当下依然需要的精神力量。 时代的大历史影响着无数的个人命运小历史。拿金一南的小历史来说,他能在57岁时奉献一部备受推崇的《苦难辉煌》,不是因为他一拍脑袋找到了与众不同的新视角,也不是取决于15年的写作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回望得远一些,在始自少年的更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在时代大历史中进行着个人小历史的能量积聚——那是一些有心的阅读、观察、体验、追问、思考、解答,进而形成思想,喷薄欲出。 这些思想能拿来做什么? “这有点像鲁迅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但熔岩什么时候喷出,从哪个口喷出?我并不知道,直到碰上《苦难辉煌》——这本书就是契机、就是突破口。” 从时代大历史中“采火”的金一南,终于将个人小历史中灼沸的“熔岩”,喷涌到了这个亟需反思、呼唤信仰的时代。 金一南在884舰上完成《苦难辉煌》定稿 采火 “‘文革’期间,我是带着满腹狐疑第一次打开《毛泽东选集》的。”金一南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没有亲历那个时代的我仅从有限的史书阅读中妄自得出结论——对《毛泽东选集》,当时的老百姓似乎只有虔诚的权利,没有质疑的资格。 “不全是这样的。父亲是开国将领,一夜之间被打倒,我成了黑帮子女,初中毕业被分到一家街道小厂当烧瓶工。在经历种种不如意和看到许多阴暗面之后,我琢磨:党和领袖真有这么伟大吗?他们当年闹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 14岁的金一南在《毛泽东选集》里寻找答案。“一旦探索,就不能自拔。不是被理论牵引,也不是被传统观点(比如路线斗争史、统一战线史)左右,而是试图用自己的眼睛看清历史的真实。”建党时才50多名党员,为什么28年后就能夺取政权?南昌起义时只剩800名军人,为什么22年后就能解放中国?绝非天意,只能是民心! 民心就是力量的本源,汇聚成为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迷乱的“文革”时期叩问民心,金一南一方面看到了党深厚的群众根基,同时内心中有一种希望,又有一种确信——党有自我纠偏能力。 林彪坠机事件让很多人的命运出现转机。1972年,金一南20岁,报名参军。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经现实和书籍的双重解答,他曾有的疑虑转化为对党和军队的信服和追随。他说了两个“一辈子”:当兵不一定能当一辈子,对这个党、这支军队要认识一辈子。 《苦难辉煌》是在军营特殊环境里酿出来的,不仅能从文本上寻找到金一南最早通读著作的影子,更能看出作者历史观的奠定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从14岁到24岁,正是历史观培养的最佳年龄段。10年间的幸与不幸,对某些人而言只是心灵上的一道痕,但金一南却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一种眼光:审视历史、挖掘历史,而不是人云亦云、概念先行,更不是遗忘、否定。 中央党校某位权威人士在分析《苦难辉煌》大范围产生共震的原因时提到一点——作者的“审美冲动”。历史,当你用审视的眼光去深挖,真的是能够审出美感、审出崇敬的。这是一种为外人不可道的乐趣。1987年,正是“下海”风潮势头最盛的时候,金一南放弃了炙手可热的部队生产部门,到国防大学图书馆当一名普通馆员——他想要挖掘的是历史的富矿。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新解密的情报整理、“老革命”的回忆录、当事人的日记、遗书等手迹……不就是一座座富矿么?金一南一头扎了进去。海量阅读,只嫌知道太少;惜时如命,只嫌日头太短。为了读懂海外评价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为了第一时间读到外文杂志,他35岁学英语。为了制作更便捷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他41岁学计算机。对他而言,学什么都不算晚,学什么又都怕来不及。别人说他自找苦吃,他只觉得乐在其中。 11年,寒来暑往。通过对正反面材料的对比阅读和对历史细节问题的分析甄别,他练就了一双去伪存真的火眼金睛,也获得了横看全球、纵看古今的大视野。 应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老话,1998年,46岁、只有大专学历的他被调到教学岗位。厚积薄发使他成为一匹“黑马”,如今已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获少将军衔,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和全军“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聘他为兼职教授……他享誉军营内外。 但他的头脑依然冷静。过去做学问,做好做坏对别人没什么大影响。现在做学问,做好做坏影响的是学生、观众等一大批人,甚至影响的是学科建设、军队建设。他说:“没有很强的紧迫感和很深的危机感,不更新原有知识,强项也会变成弱项,所长也会变成所短。” 他别无他选,唯有抓紧再抓紧、用功再用功:醉心每一个书籍相伴的夜晚,珍视每一次国外考察的机会,看重每一个学术论坛,苛求一切可能的实地求证…… “地火”愈采愈多,“熔岩”越灼愈热。 家中阅读 喷发 15年前,出版社只是想让金一南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金一南那些快要憋坏了的积累忽然看到了有个出口,便争先恐后往外冒。冒到哪里算哪里,都写了10万字了,红军还没出发呢。金一南心想,坏了,不会是跑题了吧,就拿给出版社看。出版社反而很高兴:“太好了,你就这样写下去吧。” 不列提纲就动笔写书,这听上去好稀罕。但金一南确实就是这样的。 在他看来,研读历史需要反复斟酌的哲学思辨,而当这些历史素材内化为感悟之后,不如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在艺术的领域,第一个念头最好。” 所以,当他决定把第一道目光投向国防大学图书馆角落里那本枯黄脆裂的《蒋介石日记》并以“西安事变”作为切入点之后,接下来的《苦难辉煌》往哪里张望,就全凭信马由缰的恣意了。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历史小说”、“革命史诗”来形容此书。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体裁,只知道写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体裁限制。”就这样,它表达了他心中的东西,既有恍惚间如同亲历历史的激情,又有蓦然间拉开历史景深的喟叹,那是一股在今昔时空里自由穿梭的气息,是一种对先人或崇敬或悲悯的情义。它们就这样喷涌出来,恣意的,也是最美的,不可复制的。 所以,他把它看得比命还要珍贵。那是在2006年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演期间,他在军舰上对《苦难辉煌》进行最后修改。海上编队从美国向加拿大航行途中,遭遇到了老海军前所未见的巨浪,舰首连连被埋,锚链仓钢化玻璃被打碎,80吨海水涌了进来,机关炮炮衣被撕开,舰体的钢梁和钢板嘎嘎作响……风浪持续了2天半,无法站立,无法就餐,无法睡眠。金一南护着笔记本电脑(《苦难辉煌》全部书稿都在里面),一门心思在想:“可能回不去了,可惜了这本书稿。如果有直升机能把电脑吊走……” 如果一定要把“心血”和“命”舍掉一样,那些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凝成的心血,有时候真的可以比命都重要。它存在,就已经是火热生命的见证。 它伴了他十多个年头,直到他为它画上最后一个句号。那一刻,没有欣喜,只有“怅然若失”。他太留恋每一个与它相伴的日子了! 那是一种“狂”——“那么多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但我不是‘跪’着写的,我甚至不是‘站’着写的,即使‘站’着,他们的背影也足以挡住你的视线。我写的时候非常狂,感觉自己是往下看,看他们的得失,看他们如何创造历史。” 那是自己跟自己“吵架”——“有的人写书,没有辩论,真理全在他手。而我一直在自我激辩,跟内心吵架,跟看不见的对手吵架。没有疑问,就没有思辨;没有思辨,就没有真理。宗教从坚信开始,科学从疑问开始。” 那是动情的泪——“有难以计数的英雄,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评奖、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的帷幕后面。有读者告诉我,王开湘举枪自杀和胡天陶被枪毙的那两段非常感人。这也是让我最动情的两个人,今天,他们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写他们时我流泪了。我愿意为他们流泪。” …… 我问:“写一本书写了15年,难道不苦吗?” 他摇摇头:“那是别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浑然不觉。” 他跟我说起1995年、这本书刚刚开始那会儿的一件事:他得了痔疮,动了手术,无法坐立,就把386台式机搬到地上,铺上地铺,支着胳膊,趴着写。来客一进门就喊:“哎哟,怎么这样……”他茫茫然抬起头,好像还回不到现实间。 他苦吗?不苦吧!真的不苦吗? 但我知道,为这50万字的《苦难辉煌》,他专门写了300万字的笔记:列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4条时间轴,又列了4组人物的活动。其中绝大部分素材,在《苦难辉煌》中并未提及。功夫白做了吗?这是又一次“采火”和“熔岩”的酝酿么?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不为下一次“辉煌”,只为乐在其中。 闲暇时光 奔腾 金一南“采火”之后形成的种种思考和观点,是版面之内无法一一尽述的,好在其中的一部分精华通过《苦难辉煌》传递给了读者,并随着媒体的争相解读更趋清晰。通过专访,金一南的新见解更多地呈现出来—— 英雄·人民 “沈阳军区炮十师有个‘董存瑞连’,每天点名,第一个点的是‘董存瑞’,全连集体喊‘到’,声音非常洪亮,哪怕是新入伍的士兵,跟着喊一声,立刻就能感染到那股豪气。 “英雄的豪气是一种气场。进入英雄的群体,哪怕是懦夫,也会变得勇敢;相反,进入懦夫的群体,哪怕是英雄,也没有用武之地。一个贬低、轻视英雄的民族,不可能完成复兴伟业。 “有人说,时代变了,英雄观也要与时俱进,不用再讲狼牙山五壮士了。英雄会变得陈旧吗?狼牙山五壮士是在民族命运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候迸发出的强烈光芒。如果对这个都不珍惜,那还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 “我们讲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人民中那些最早觉悟、奋斗最为英勇、牺牲最为坚决的人,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创造历史’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都是通过人的牺牲奋斗去实现的。没有牺牲奋斗,所有东西都是虚的。”
假想·潮流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最理想的是‘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错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宣称这种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强大了。那些认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倡导者康有为‘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能否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其三,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须兼备物质、精神的双重强大。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枪杆子·民意 “2001年我在美国讲学,有个美国人质问:政权是选出来,不是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当时就问他:‘第一,你说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请你告诉我,美国从最初的13个州发展成50个州,哪一个州不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先打印第安人,再打墨西哥人,后打西班牙人。如果有例外,就是从法国人手里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从俄国人手里买了阿拉斯加州。靠的都是金钱和武器,哪个州是投票投过来的?’这个人回答不上来了,我看他对美国的历史还没我熟呢。 “我接着又说:‘第二个,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才50几个党员,建军时800来个军人,就那么点儿人,而国内资源和绝大部分的国际援助都在对手手里,她能够用20多年时间把盘子翻过来,没有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可能吗?那时老百姓不知道用手投票,但他们用双脚投票,用行动投票,推着小推车,把物资运往前线支援解放军。’ “现在,我们有一些干部忘掉了执政的根本,做点好事就像是给群众施恩。这时候回顾苦难史,其实是在回溯力量的本源,提醒我们的政党千万不能背弃根本,一旦背弃就会被历史背弃。 “82年前,毛泽东发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叩问,中国红色政权今后如何存在?新一代共产党人还要继续这个命题。2008年,法国《世界报》有篇评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表现出了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可塑性’这三个字评价很高。怎么塑?怎么变?民心是一杆标尺。”
满·“飞白” “在历史大命运前无法主导个人小命运,这是一切悲剧的根。就拿中国革命来说,多少人因它获得名誉,多少人因它毁掉名誉,就全看你是不是顺应了历史。 “历史富有大量的戏剧性场景,比如:1934年,红色首都瑞金被两个前共产党人李默庵、宋希濂占领,他俩是黄埔一期的早期共产党员,‘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脱党;14年零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的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前国民党军官。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奇伟,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他在后面追了2万余里;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传统史书的写法是,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一一记录,看似很满,但它不跳跃,不会从1934年、1935年一下子跳跃到1949年。就拿我上面说的4件事情来说,时间上不挨着,就往往被拿来单说。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对比一下呢?为什么不在‘吴奇伟追袭2万余里’之后加一句‘1949年10月1日他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呢?只要加这一句,别的不用多说,就像国画当中的‘飞白’,那会激起读者多少想象和感慨,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报复,也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眷顾。如中山先生所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也许我是研究战略的,和史学家看历史的方法不大一样。在我看来,历史的一些细节是可以省略的,但某些细节绝对不能省。 “再讲另外一件让我很受触动的事。我在2006年参加了中美首次联合军演,到达夏威夷后,我提出要去看看张学良的墓。当我看到那块除了姓名和生卒之外任何记录都没有的墓碑时,很惊讶,为什么不去竖个丰碑,刻一篇长篇大论的碑文呢?疑问之后又生出感慨:真正的大人物需要碑文来证明吗?是非功过不全在‘张学良’这三个字里面了吗?在我看来,那块草丛中的张学良墓碑就是一个不能省略的细节。”
附:红军长征路线成为全球最具魅力的中国之路 ——读《苦难辉煌》 众石 美国作家斯诺在上世纪30年代冒险跑到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曾一举在美国掀起“红色热潮”。50年后的198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在76岁高龄、怀揣心脏起搏器跋涉两万里,写就《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之后,世界各地不少“年轻的背包客”来到中国,把红军长征路线选为全球最具魅力的徒步路线之一。红军长征的故事,如同大海的波浪一般,每到一定的时刻,就总是在人们内心深处掀起巨大的波澜。 最近,一本讲述中共早期革命历史的新书《苦难辉煌》一年多来连续13次印刷,在当当网上一度占据军事类小说销售量排行榜第一位,被评为五星级图书。网上调查称,喜欢此书的读者占98.8%,94%的人认为看了该书以后“受益匪浅”、“过瘾”、“感动”、“开心”。 在金一南教授这部还原历史真实细节的52万字大部头里,处于胚胎期的中共和后来的长征历程,第一次被置于全球战略博弈的大格局下,并被进行精心而深刻的梳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纷争与联合,与日本侵略势力的浴血对抗和激烈博弈,以及其背后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力量及苏联国家利益搅揉搀杂的复杂背景,这一切,勾画出了一幅动态的变化的斗争的生动历史画卷。而进行伟大远征的红军,正是在多股力量的夹缝中,依靠自己强烈的使命感和绝地求生的意志,闯出了一条艰苦卓绝的“中国之路”。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对红军四渡赤水的描写。从真实的历史看,那正是红军长征途中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而在四次渡过赤水的战略性转移中,红军并非每次都“用兵真如神”。至少有两次,是在决策失误或作战任务无法完成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退却。作者说:其实没有神。红军中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个人。人最不能避免的就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后人“好心好意”的回避,把人拔高成无往而不胜的“神”,恰恰把共产党人最富有生机的灵魂抽掉了。这个灵魂不是佛光神意,而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实践精神。 事实上,《苦难辉煌》里力透纸背的战略思维,可能是吸引当代青年读者最重要的地方。已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两方面全球化的当代中国青年,对国际政治和历史的认知方式,也已经本能地倾向全球化的战略思维。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和方法天生具有“博弈精神”。他们崇尚力量,推崇技术,仰慕英雄,赞美那些集力量、意志和理想于一身的“实干家”。这些了不起的人物,要在具体的现实的残酷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红军长征的大历史,包含了丑恶与悲哀,没落与衰败,牺牲与献身,光荣与梦想,都浓缩在这样一次烈火真金的考验里。 可以把《苦难辉煌》当做一本当代中国青年培养地缘政治分析能力和“全球化”战略思维的训练手册,观念的种子由此埋下。这使他们习惯于“研究地球问题”,而不仅仅把目光限于一国之内,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也不再是单线条的,而是立体的、多维的和宏观的。他们将学会把中国的崛起放在一个大范畴的历史框架中加以解读。这样一段波谲云诡又激情狂飙的真实历史,怎么不让他们心潮澎湃! 在金一南教授笔下,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养生。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领导南昌起义。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聂耳为今天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不到23岁。一个1921年成立、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党,28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一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立、最后只剩不到800人的队伍,22年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一切,无不叩动着当代青年的心灵,牵引着他们的思绪。 索尔兹伯里曾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有西方读者把长征与《圣经》中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远徙相对比,称之为20世纪最叩人心扉的东方远征。今天,读过《苦难辉煌》的中国网友给作者留言,“渺小与伟大、卑贱与高贵、阴谋与阳谋共存,冷血与热血、低潮与高潮、失败与胜利交织,波澜壮阔,伟哉中华!”更有人感慨说:“商业大潮的汹涌已荡涤了国人的灵魂,谁还为思想而累,为激情而歌?”我们终于懂得,当个人的命运同一个国家的崛起紧密捆绑起来,当个人的理想同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充分结合起来,人由此进入历史,也将创造历史。
推荐人:lry 2010-09-06 执行编辑:tmy 2010-09-07 责任编辑:zjy 2010-09-08 |
| 0 |
|
相关评论: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暂无相关信息
当前位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