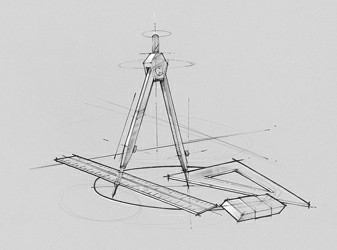|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 |
|
登录日期:2012-09-27 【编辑录入:wangdl】 文章出处:文汇报2012-09-27 D文汇教育•校园版 |
| 有一些真理,似乎已被淡忘 |
|
作者:苏步青 姜澎 洪家兴 苏德明 李大潜 沈纯理
阅读次数:13001
|
有一些真理,似乎已被淡忘 ——怀念苏步青先生 今年9月23日,是苏步青先生110周年诞辰。苏步青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被尊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他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即使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也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身体力行地演绎着一名教师的崇高师德。 在1931年至1952年的21年间,苏步青培养出106位毕业生,其中建国之后担任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就有30多位。但在更多晚生后辈心里,苏先生不仅有让人高山仰止的学问,更有虚怀若谷、求真务实的人格魅力。即使是那些定格在学生心中的关于先生的小事,也桩桩件件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聆听先生弟子和亲人的讲述,宛如重温一段关于大学的回忆——有很多治学的真理和人才培养的基本道理,我们本不该淡忘。 本版文字整理:本报首席记者 姜澎
【经典语录】 “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用不着等待什么特殊机会,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表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登贵在少年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我们老年科学工作者能否正确对待这个规律,并自觉主动地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不必为学生超过自己而感到羞愧难受,而相反地应把它看作是对四化建设的一种贡献。”
“语文与数学” “我是研究数学的,对语文也有很深的爱好。我小时候在家乡放牛,常骑在牛背上念《千家诗》,稍大一些,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随后我对古文发生兴趣,爱读《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等名著。有一回,学校来了一位数学老师,上数学课,讲得非常引人入胜,把我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受老师的影响开始爱好数学,数学成了我一生研究的对象。这当中,虽然有些偶然性,但老师能把学生吸引住,还不是借助于语言的魅力吗?虽然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数学,但我们没有放弃古诗文的学习,时常写点诗,既丰富业余生活,又练了自己的文笔,对写论文也有很大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我今年已经81岁了,写字还是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而看到一些青年的来信,不仅字迹潦草,而且经常有错别字,这也是不重视语文学习的表现之一。有时我看到这种信,常常退回去,因为这根本是不让我看嘛。” ——摘自《略谈语文与数学》作者:苏步青
“语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 “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宣言”
上课是一名教师的天职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1985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在答辩结束后,苏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懂了,我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种答辩会。”…… 洪家兴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历任教育部部长上任时,都少不了号召教授到第一线给本科生上课。可说归说,做归做,从也没有真正执行过。苏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上课是一名教师的天职。
他到哪里,哪里就发展神速 在50年前,我就听苏步青先生教授几何课。苏先生讲课十分幽默,时而会穿插一些著名数学家的趣事轶闻。他的板书十分工整,几何图形画得非常漂亮。当时,苏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主管教育工作的副校长,公务繁忙,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兼职,但他总是一门课从头到尾亲自上,不请任何人代课。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1985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结束后,苏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懂了,我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种答辩会。”我们在座的学生都很震惊。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苏先生就是我的偶像,进了大学之后,我知道他的学问一直处于高山的顶峰,对我们后辈而言真是高山仰止。可他公开说,他一点都不懂,再也不参加这样的答辩会。怎么回事? 过后我想想,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如果仍然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学科几十年来没有发展,或者已经走向死亡。所以,苏先生的话,是说出了一个真理,但这个真理,今天似乎越来越被人淡忘。 所谓“饮水思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些“乘凉者”常想一个问题:自苏先生1931年从日本回国、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后只有区区十几年时间,但到40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参观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时,却发出“这是东方剑桥”的感叹,这是为什么?那时,学界已有“北有清华、南有浙大”的说法。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苏先生和陈建功先生来到复旦任教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数理系底下的一个数学组办成了国内最好的数学系之一,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北大数学系、中科院数学所一起,在中国数学界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什么在他的推动下,发展会如此神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下,探索苏先生走过的历程,会给我们很多启示,而这些启示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科学家,无条件报效祖国 苏先生身上,始终体现着一位科学家的赤诚爱国之心。苏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放弃了在日本的优越生活,应聘浙江大学。当时,他领受的“当头一棒”是,学校四个月没发他薪水,因为发不出薪水。甚至其时出现河南水灾,国民党政府决定公债还要用教授的工资去抵。尽管如此,苏先生毅然决然地把日本夫人和孩子接回了中国。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湄潭,苏先生一家八口生活困难,靠开荒种地和地瓜蘸盐巴为生。这样的条件下,他也没有放弃培养中国数学系和数学人才的梦想,在昏暗的油灯下通宵从事科学研究,感染着周围一批年轻的学生,激发他们从事数学研究的激情。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就是在苏先生的精神感染和刻苦钻研下建立起来的。 从苏先生的经历中还可以看到一点:一个学科带头人,应该把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苏先生无论是在当他系主任、副校长还是正校长期间,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抓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人们对“左”的思潮还心有余悸,苏先生在参加邓小平组织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带头发言,痛批“四人帮”,并提出要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百废俱兴,队伍建设先行。他从浙江大学转到复旦大学时,最大的顾虑是,能不能在复旦重建他在浙大的微分几何队伍,考虑的还是队伍建设问题。
青胜于蓝,教师一生的目标 苏先生待人豁达,胸怀宽广,有海纳百川的个人魅力。我常听老一代数学家说,苏先生多次提到前辈姜立夫的重视和提拔。在谈到陈建功先生时,他经常满怀激情地道说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陈先生对他的帮助。我还听比我高两届的学长说,60年代苏先生给他们上微分几何课时就告诉他们,中国人中有一个几何做得很好,比他还好的人,他叫陈省身,在美国。 苏先生的身上完全没有所谓“文人相轻”的味道,他一直赞美同行,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年轻人,苏先生一直是尽心尽力提携。当学生在科研上取得初步成果后,他表现出特别的喜悦,会帮助他们修改论文、改写英文,并把它们推荐给国外的大师,或到重要的期刊上发表。苏先生把“名师出高徒”改为“严师出高徒,高徒促名师”。这些充满哲理的话,体现了他的谦虚和大家风范。 苏先生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作为一生奋斗目标,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学生这样做。他在科学研究上严谨治学、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举不胜举,值得我们今天的晚生后备缅怀、学习。
他“啪”地把论文甩下去,让学生回去改 苏德明 苏步青之子、复旦大学教授 很多人提起父亲,都说他是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但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热爱我们国家。这和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父亲出生在农村贫困家庭。我祖父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学校去念书,但念完后,家里太贫困了,无法继续深造。于是,当时的校长就自己掏了两百个大洋,送他去东京留学。一个校长能够拿出两百大洋送学生到日本去留学,这种事情即便到了今天,大概也不多见。父亲去日本时大概只有17岁,他最初念的不是数学,而是电机系。毕业以后,他发现自己对数学有兴趣,就转到数学去了。 正因如此,父亲后来对自己的学生也非常好。从父亲到他的学生谷超豪先生,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直到自己步入老年,还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并且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父亲是这样对自己的学生的,所以他的学生也用同样的热情和关爱对待自己的学生。 当我们家还在浙江时,我们就住在数学所对面。每个学生,他都要去家访,了解他们的家庭和学习情况,也定时和自己的学生谷超豪先生沟通学习情况。后来,谷超豪先生也是如此。 当时谷先生也一直要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在杭州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周围的几个男生,是谷先生家访的对象。谷先生往往家访完了,就来找我父亲交流。他都是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肚子早就饿了,看着谷先生老坐在那里,谈个没完,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他的“屁股长”,坐在凳子上起不来。 但我想,我们现在“屁股长”的学生恐怕不多了,而我们的老师也没那么多的空跟学生交流。 父亲把自己的学问教给学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使得大家亲如一家人,甚至比一家人还要亲。这一点,是他培养人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父亲对学生很好,但是也很严厉。他是有名的严格,年轻的时候恐怕是蛮凶的,后来年纪大了,脾气好一点。很多时候,他严格是因为他仇恨错误,认为你不应该犯那样的错误。有的学生年纪蛮大,早就是大教授了,父亲一看稿子不行,“啪”地把论文甩下去,让学生回去改。虽然有点粗暴,但是他对学生非常重视。 有人曾开玩笑似的叫父亲为“数不清”,说他的学生多得数不清。实际上,他更加注重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父亲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时,树立起严谨治学的学风。记得那时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女学生,过不惯浙大紧张、清苦的生活,开学不几天就溜回繁华的上海,看电影、串亲戚、会朋友。后来,她在父母的催促下回校上课。父亲那天一进教室,就点名叫她上讲台演算习题,算不出不准下讲台,一直在黑板前“挂”了一个多小时。从那以后,她的全部心思都用来学习,后来成了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 “一生著述开宗派,百载树人播馥芬”,父亲年逾八旬之后,仍然关心青少年的学习和思想。有一天,他收到一位小学生家长的来信,反映他的孩子对一道数学题的理解。这道题说:“有8个队,每队5人,一共有多少人?”孩子用“8×5”的算式来表示,老师说不对,应该是“5×8”。这位工人家长不理解,特地给数学家苏步青写信。父亲立即给他回了信,讲清楚这个问题。后来,那位家长很感动,就将苏步青的回信交给了《文汇报》。不久,《文汇报》用很大的篇幅,全文刊登了家长的来信和苏步青的回信。《文汇报》上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还能关心科普工作,足见他对青少年的关怀。父亲则认为,青少年是祖国的将来希望所在,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的成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竟微服私访,听了一堂我上的辅导课 李大潜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每次想到苏先生,我的记忆总绕不开那几件小事。它们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都是苏先生留给我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时而让我感到无比充实、幸福。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大学毕业后刚留校任教的时候。那时,对于怎样做好一个大学老师,我心中很没有底。有天晚上,我专程到苏步青老师家中登门请教。他当时讲了很多,但我牢牢记住的是他说做学问“贵在坚持”那四个字。他接着现身说法地作了详细的诠释,说他自己不论多么繁忙,每天至少要坚持学习两个小时;如果有一天实在做不到,第二天也一定要设法补回来。他还介绍自己平时如何挤时间学习的一些窍门和方法,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不到一个誉满天下的大数学家竟还如此刻苦认真地坚持学习,那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发愤图强吗?!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大学毕业、从宝山葑溪乡劳动锻炼一年后返校任教的最初日子。1958年数学系的大学新生有八个班,近250人,我担任他们解析几何课程的助教,这是我首次担任教学任务。这个年级新生中,有不少同学来自工农业生产一线,学习相当吃力。但那时,教师和学生们都响亮地提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口号,大家的热情很高。不久,我给学生上了一堂辅导课,将大课上讲的好多内容和公式作了归纳,理清思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我自己也相当满意。下课后,我惊讶地在教室最后一排发现了苏步青老师,想不到他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微服私访”,从头到尾听了我上的这堂辅导课!他虽然没有对我这堂课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和批评,但我也从来未听说,他还会有空来听课,竟出现在我的讲堂上! 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警示和教训,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教师,尽心尽责、精益求精地搞好教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决不能漫不经心、粗制滥造、随心所欲。
第三件事,发生在我即将第一次走出国门、赴法国进修的前夕。那是在1978年底,我即将由北京飞往巴黎,而老师也恰在北京开会。他主动提出利用会议的休假日带我游北海公园,为我送行。冬日的北海并没有太多的诗情画意,但我们却玩得很开心,一起登上白塔远眺北京城内的景色,还拍了不少照片。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心情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凑成一首七律送给老师,请他斧正。意想不到的是,他也专门写了一首七律赠送给我。这首七律的后面四句是: 此日登临嗟我老, 他年驰骋待君还。 银机顷刻飞千里, 咫尺天涯意未阑。 我知道,诗中“他年驰骋待君还”句,是他、也是复旦对我的期望和鼓励。
80岁的他,竟还想着换个方向做学问 沈纯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57年,我考进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时,苏先生已是复旦大学副校长。 此前在中学,我的数学学得不错,但大学里一接触数学分析,觉得题目难得很,对数学的兴趣大不如前,所以想转去化学系。我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苏步青副校长,提出了我自己的想法。 这封信发出后,我就后悔了,觉得自己闯了祸。因为苏先生是数学系的,我还这么抱怨数学难学。果真没几天,数学系的老师就来找我,说:“你寄给苏先生的信他已经收到了,也看过了,他有一些话通过我来转告你。”虽然说的那些话无非是鼓励我不要怕困难,要继续学习,但是也提到了一些数学学习的方法。这说明,苏步青先生对于一般学生学数学的苦恼也是非常关心的。 大四时,我被分到几何专业组,那时的微分几何概论等课程都是苏先生亲自上的。他讲课非常精细,板书工整,也有讨论。在讨论中,我得到了苏先生的很多指导。 后来我念研究生,更有机会得到苏先生的直接教导。有一次,苏先生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就说了一些我对数学课题的想法。他当即鼓励我把它写出来。我写完后,他用红笔修改,然后推荐我投到当时的《复旦学报》去。 “文革”结束后,1980年左右,我有事到苏先生家里去拜访,那时他已经80岁左右了,还在家中做科研、写论文。我很感慨,我们到80岁不知道能干什么。而且当时苏步青先生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计算几何。因为在“文革”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江南造船厂,遇到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因为有着射影几何的背景,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和现在的计算几何有关系。一个人到了80岁,还想着换一个方向,研究和实际有关系的学问,这一点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荐稿人:wdl 2012-09-27 执行编辑: lxl 2012-09-28 责任编辑:lry 2012-09-28 |
| 0 |
|
相关评论: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暂无相关信息
当前位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