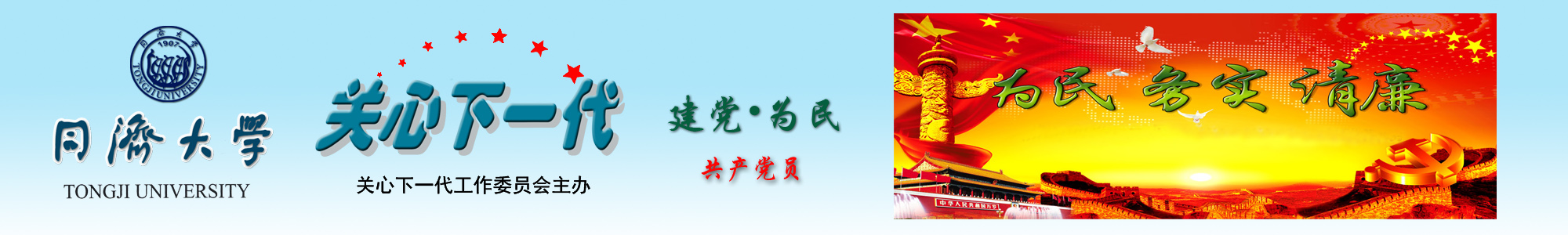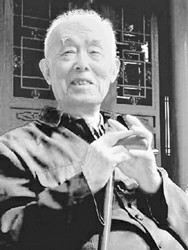|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 |
|
登录日期:2009-08-02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文汇报》2009年7月13日第8版、7月26日第8版 |
| 季羡林 回忆 |
|
作者:范昕摘编
阅读次数:68155
|
风风雨雨一百年(絮语) 谈往事 我仔细读了读这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后者仿佛记流水账似的,刻板可厌,间有写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却写得丰满,比较生动,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一些将近七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子时写的东西。我当时已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但是,那些东西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在有意无意间有点忸怩作态,有点做作。日记却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有像李越缦写日记时的那些想法。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蔽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这多一半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不能怨天尤人。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彼此彼此,我并没有多少怨气,也不应该有怨气。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谈生活 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谈人生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听说还有人正在写作。至于单篇的文章数量更大。其中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当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别人写的传记和文章,我基本上都不看。我感谢作者,他们都是一片好心。我经常说,我没有那样好,那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在病中》 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谈治学 被戴上“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谈长寿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长寿之道》 荐稿人:lry 2009-08-02 执行编辑:xwf 2009-08-05 季羡林风风雨雨一百年(自传) 2009年7月11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载人生历程,含笑西去。 ——引言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我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我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季羡林精神遗产 他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忠恕,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开放创新的意识有机地相结合,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一个世风浮躁、大师短缺的社会转型期,季羡林先生带着他对整个20世纪的思考、对21世纪的美好憧憬远行了。 然而,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除了他对中国学术、乃至世界学术的巨大贡献之外,首推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的“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的预言。季先生在20年前提出这个预言时,正值近代以降,第二次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涌动之际,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以为,这是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孰料20年后的历史在证明着他的预言。 为了弄清季先生提出这个命题的思路,我曾对他作过专访。 那是2001年岁末,初冬的京城下了第一场瑞雪,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朗润园显得格外寂静、空灵,人行其间,有一种超然之感。就在这个曾是前清“万园之园”的一幢陈旧小楼里,慈眉善目的季先生心鹜八极,思绪翱翔九天,谈了自己对东方文化复兴的识见。 季先生提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的论断,并不是他心血来潮,信口拈来,而是基于他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和思索。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时,先从宏观入手,让人循着他的思路一步步去认识他的论断。 季先生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乃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交融、东西文化走向的比较、中印文化的交流等三个方面的思考。 季先生首先指出,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都离不开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其背后实质是个文化问题,也即归根结蒂是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的前进。从这一点出发,人们特别要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他认为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也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体系、希腊文化体系。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它不是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就是和希腊文化体系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而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因为文化交流能促进交流双方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发展,能增进双方科学技术的兴盛。文化的交融之所以能推动双方社会的前进,还基于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总之,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在推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 季先生接着说,在21世纪,东方文化正在走向复兴,西方文化则走向衰落。他认为,人类跨入新世纪后,需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特别要反思曾经有过的一些不确切的概念。我们曾陶醉于“中国中心论”,明清以来,诸多封建帝王自诩“天朝第一”,结果却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后来又有人提出“全盘西化”,其实这是“西方中心论”,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再来看东西方两大文化的概念。从宏观上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相互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和消逝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和消逝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不可能永世长存的。在今天,西方文化因其某些弊端,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 至于东方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这可以从东西方哲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入手,进而梳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产生那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总的说,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这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但是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这可以从模糊学和混沌学上得到印证。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季先生坚信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季先生最后特别强调,21世纪东方文化之所以将全面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融合。季先生推论这一观点时,也是从中印两国的思维模式切入的,他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伴随着中印两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一方面,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从中印两国交流的特点来说,季先生认为是时间长,涉及面广。两国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的交流,近年来也有考古新发现。涉及面广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交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则有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推而广之,中印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思维模式更趋一致,从而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也即势必影响到东方文化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在人类历史曲折前进的今天,回过头来体验季先生的预言及其推论,应该明白他的预言、他的思索是辩证的,他是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忠恕,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开放创新的意识有机地相结合,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资料来源:2009年7月26日《文汇报》第8版 荐稿人:lyl 2009-07-27 执行编辑:lyl 2009-07-27 责任编辑:tmy 2009-07-28 |
| 0 |
|
相关评论: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暂无相关信息
当前位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