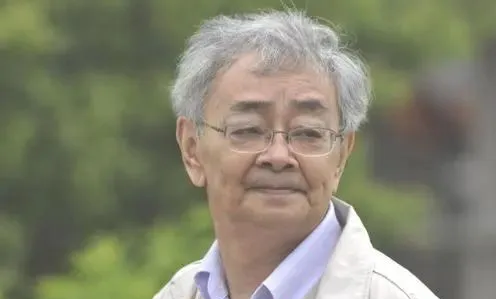|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 |
|
登录日期:2020-05-06 【编辑录入:wfiwfi】 文章出处:上海采风 |
| 我所见所闻所思的老吴 |
|
作者:陆寿钧
阅读次数:19875
|
1、题解
无疑,吴贻弓以他的为人为艺,被我国电影界公认为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群体中的领军人物。我尊重他一贯的谦逊,特再加上“之一”两字。 无疑,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吴贻弓从1984年46岁起,至2012年74岁止的28年内,被当过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第六届市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艺术总监、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高官要职。我却很少听到老上影人叫他吴局长、吴厂长、吴总、吴主席的,一般都以摄制组里的叫法,亲切地称他为“吴导。他大我四岁,我们编剧又很少下摄制组,我则称他为老吴。这样的相处,我们彼此都舒服。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能这样叫他,当然舒服,而在他而言,能如此看淡官职,是非常不容易的。他74岁完全退下后,用了“申江小吴”的网名,在网上交了很多普通的网友,似乎感到更舒服,则更不容易。 无疑,老吴一直以普通人为乐,在他离世时,也不愿惊动大家,只想悄然而去。我的这篇悼文则题为“我所见所闻所思的老吴。
2、我的三篇日记
2019年9月14日,星期六。 刚过完中秋节,一早,上影公寓中就有人告诉我:网上发出了讣告,吴贻弓于今晨逝世。虽大家都知道,他已进医院好久了,但总认为他会有惊无险,康复出院的,所以,对这个噩耗,大家都目瞪口呆…… 我们一些退休的老上影人,自发地聚在一起,追思着他生前大家一起与他相处的日子,无论是创作人员、一般的工作人员,还是他属下的干部,都有着美好的回忆,可见他的为人为艺。 网上还登出了他临走前写下的一句祝愿:“上海电影万岁!”我太熟悉他的字迹的,而这六个字加上他的签名与书写的日期,已歪歪斜斜地有些走形,看得出他那时的身体状况。在那样的时候,他还想到艰难地要写下这样一句话,含义令所有上海影人们可敬和深思。我能体会到他此时此地的心情。 一到晚上,一天内已有不少人在网上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悼文。而在我心目中,他永远定格在我对他自始至终的称呼“老吴”两字上。他也跟着大家一起叫我“大陆”。而如今,我再也无处去叫他“老吴”了,也听不到他亲切地叫我“大陆”了。我会好好为他写篇悼文的,但不是现在,需要时间能让我“痛定”,再“思痛”时,肯定能写得更贴切些——
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 两天过去了,还没有何时开老吴追悼会的消息,我打电话给上海影协原常务副主席许朋乐询问。他说,他也感到奇怪,刚给老吴儿子天戈打过电话。天戈的回答是,遵照他爸生前的关照,后事一切从简,不想麻烦任何人。朋乐与我都为此事感叹万分…… 我这个人,在感情上较脆弱,在得知老吴去世的第一时间里,不敢给文蓉大姐和天戈打电话致哀,更不敢冒然提了个花篮去他家吊唁,只想去参加追悼会来表达我的心情。如今,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给他家打电话致哀了。我还是不敢面对文蓉大姐,怕她太悲伤。我先找出天戈的手机号码打去——13301612929,回答是空号。我只得再打他家的座机,是文蓉大姐接的电话。我讲明了情况,还不及我安慰她,她就告诉我,这是老吴家的传统,上一辈都是这样从简的。我问:家里也不设灵堂?她说:不设,真的一切从简。一下又堵住了我去他家吊唁的路。她告诉我,老吴走得很安详,如睡去了一般。他已有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了,医生让天戈找张纸来,让他写下想说的话,他就写了“上海电影万岁”几个字,还签上了名,记下了日期。这是他最后想说的话,说不出了,就写。写的力气也没有,从字体上大家都可以看出……接着,文蓉大姐反倒安慰起我来,她说:老吴知道你对他的感情,他进医院前你来看他,他很高兴。你也尽了情了,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多保重身体…… 我是含着泪放下电话的。为电影奋斗贡献了一生、我们这代电影人的领军人,就如此悄然而别了?
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 上午,去青浦福寿园参加老吴的葬礼。去的人很多,都是主动、自愿去的。 落葬前,先在一间小会场内共同面对老吴的骨灰盒开追思会。由福寿园的司仪主持,完全纯属一般普通人家的葬礼,不是哪一级组织举办的,也没有哪一级领导出席,来者都是老吴生前的亲朋,却不但满座,还有好多人站立着。座位都让给了老年人,站着的都是中青年,肃然却又温馨。大家先瞻仰了一部由天戈制作的有关老吴生平的纪念片,全是介绍他执导过的作品,只谈艺术成就,不吹官职殊荣,朴实无华,亲切感人。 接着,有三位嘉宾作专题发言,一是福寿园的一位开园元老,介绍了老吴生前对这个人文纪念公园的关心和支持,他能让电影老艺术家们在这里安息做了大量的工作;二是上海影协的一位工作人员,诉说了老吴在任上海影协主席期间所作出的贡献;三是老吴的老同学、好朋友倪震教授特意从杭州赶来,剖析了老吴在电影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由天戈致辞时,他很得人心地说,他愿把这段宝贵的时间留给他爸的同事们,他知道他们与他爸共事了几十年,今天纷纷赶来为他爸送行,是有好多话想说的。 于是,大家都抢着发言,有上影的老厂长于本正、朱永德,有一直为老吴当副导演的成家骥,有老吴的合作者作曲家金复载,有制片钱祖德……其中,最让大家感动的是两位普通人的发言:一是烟火车间的老工人钱阿发。他说,他为吴导的影片搞烟火时,吴导总来到现场叮嘱他:“别急,慢慢干,安全第一。”他说,他搞了一辈子烟火,冒了一辈子生命危险,除了吴导外,没有一个导演对他说过这样知心的话,有的还要催他快点快点。为此,他一定要来送送吴导。就这么几句,也足以让人感动了。 据我所知,在老吴最后一次进医院前,阿发师傅也曾去他家看望过。另一位是老吴读中学时的老同学的发言,他告诉大家,老吴在中学时期就是一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当时是五分制,满分是五分,他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还是学校的足球队队员。他成名、当官后,中学同学聚会他总与大家一起平等欢乐地相处,如遇拍片来不了,他也总会在片场打个手机向大家问好。也是寥寥几句,又足以勾画出老吴的为人……自由发言者都很知趣,不敢多占用时间,只挑心里话说,就这样,好多人还抢不到发言,到了落葬时刻,只能一同来到墓地。 老吴的墓坐落在上影已故老艺术家的墓群中,普普通通,一点也不显眼。但他不会寂寞。 在整个葬礼中,与老吴一起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伴、电影表演艺术家文蓉大姐,显得十分镇定,待到老吴落葬后,当她抚摸着墓碑上老吴的遗像时,却再也忍不住地泪花直流……此时,在肃静的墓地中,只听见一片唏嘘声。我边擦着泪水,边想起了老吴为我《人去影留》一书所作的“序”……
3、老吴“序”《人去影留》
我常会因内心的冲动去做一些明知力所不及的事。2009年,我把写下的几十篇已故上影师友的文字,整理成一本题名为《人去影留》的书,在上影建厂六十周年时以志纪念。我想得很好,以为做这样一件事,肯定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然现实却是那么的骨感。后来,在上海影协和福寿园的支持下,终于出书有望了。于是,我来到老吴家中,请他作序。我说:“此书非你作序不可,你是上影的老领导,见证了书中那些人的人生,你应该有责任并乐意为此说上几句话的。”话说得有些横蛮、无礼,老吴却认为合情合理而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认真看完了书稿后,写下了以下的“序”—— 前不久,大陆一一一陆寿钧专程来访,送来他近期新作书稿一部,约我为之作序。 我和大陆是上影厂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在上影厂,凡认识他的人都习惯叫他大陆,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的确不小,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待人的宽厚和大度。记得当年我心系影片《阙里人家》前期文学创作之际,大陆作为上影厂文学部的负责人之一参与其中,和另几位作者一道,组成剧本创作的中坚力量,朝夕相处,前后在一个摄制组里共事长达一年之久。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整个文学剧本的创作过程中,他时常会从反面提出许多不同见解,引发创作组成员在反复的换位推敲中不断开掘出生活素材里蕴藏着的深层内涵。于是,一个个人物形象开始丰满起来,故事也变得有滋有味了;就这样,原先的一枝小苗,在众人的精心培育下,渐渐地也就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一次和大陆的合作,无疑在我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从十多年前,我转到文联供职之后,大体上就和电影创作日渐隔膜了。其实,认真而论,不仅和电影创作隔膜了,就是和当年一起共事过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也渐渐隔膜起来。其间偶尔光顾久已疏离的上影厂,一路流连过去,自然就会遇见不少年轻的陌生面孔。然而我和大陆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却从未间断过。 这次大陆送来他的书稿,名曰《人去影留》。其中集掖着40余篇人物回忆,都是他专门为这些年来已经相继辞世而去的原上影厂各部门的老同事写的。那天,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本书,他早就想好了,是非请我作序不可的,因为,他觉得,我见证了书中写到的那些人的人生,而且,他相信,我也是有责任并乐意为此说点什么的。 的确,当我仔细读完这部书稿以后,我不禁深受感动。我觉得我无法推却大陆的真诚之请,我甚至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因为大陆是我的好朋友,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书中写到的那些人的确也曾经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辈和朋友。有的可以说大名鼎鼎、尽人皆知,但也有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幕后英雄。在大陆饱含深情的笔下,那一篇篇朴素无华,时而浅唱低吟,时而慷慨激昂,甚至近乎呐喊的回忆和纪念文字,读来无不令人震撼、感佩。 大陆在他的书稿“前言”中写道: “铸成中国电影的辉煌,不是几个人的功劳,而是前赴后继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尽自身之力,添光加彩,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更值得大家怀念。” 他在书中还这样写道:“我想,倘若这一切什么都没发生,该有多好!发生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少受心中的煎熬。既然我已知道,我就应该把这些全都写出来。”“我想,还会有好多人记着他,至少是我!”…… 是啊,世间情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执著更令人心动,又令人心痛的呢!这部书稿不仅使我重新置身于那隔膜已久的环境氛围之中,而且还使我回到了当年那些目日夜夜携手并肩的师长和兄弟姐妹们身边。所以,在这里,我要由衷地对大陆道一声谢谢!感谢他在上影建厂60周年的时候为我们送来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记得在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中国电影在过去的一百年来之所以创造出数度辉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电影有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从业者,他们以赤子之心为这事业奉献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以自身人格的魅力为后进者树立着榜样。于是,中国电影才得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于世界电影之林独树一帜。” 我忽然又想起,好像哪位哲人说过,大意是:“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 于是,当我怀着敬意,慢慢合上手中这部沉甸甸的书稿的时候,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念道:让我们的事业,就像大陆——陆寿钧在这本书中忆及的那些老上影人为我们留下的不朽业绩那样,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再从现在延续下去,一直到永远吧。 吴贻弓 2009年5月5日
据说,名人的序,价位很高。而我的拙作纯属“公益”,印了二千册,大多分送给了上海影协的会员,我不拿一分稿酬。老吴的“序”,当然也没拿过一分钱。我也从未对他作过解释,他也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说。但在我心中,他的这篇序,字字值千金,尤其他最后写下的一段文字:“‘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于是,当我怀着敬意,慢慢合上手中这部沉甸甸的书稿的时候,不由得心里默默念道:让我们的事业就像大陆——陆寿钧在这本书中忆及的那些老上影人为我们留下的不朽业绩那样,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再从现在延续下去,一直到永远吧。” 重温这段话,让我能深刻地去读懂和理解老吴临终时所写下的“上海电影万岁”那六个字,他希望上海电影的优良传统能永远延续下去。重要的是要做好每一个“现在”,这样,“过去”才会有“归宿”,“未来”才会有“渊源”。“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每一代上影影人都应日日拷问自己:我们做好每一个“现在”了吗?! 为了报答老吴十多年前为我的拙作所写下的这篇序,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以见证者和幸存者的身份,在为逐一逝世的老上影人写悼文,来证实老吴所说:“中国电影在过去一百年来之所以创造出数度辉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电影有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从业者,他们以赤子之心为这事业奉献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以自身人格的魅力为后进者树立着榜样。于是,中国电影才得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于世界电影之林独树一帜。”我已准备好以《大实在》为书名,再出一本书,再请老吴写个序。真想不到,老吴会……此痛,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4、我平生最愉快的一次创作经历
老吴在那篇“序”中,一上来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往事:“记得当年我心系影片《阙里人家》前期文学创作之际,大陆作为上影厂文学部的负责人之一参与其中,和另几位作者一道,组成剧本创作的中坚力量,朝夕相处,前后在一个摄制组里共事长达一年之久。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整个文学剧本的创作过程中,他时常会从反面提出许多不同见解,引发创作组人员在反复的换位推敲中不断开掘出生活素材里蕴藏着的深层内涵。于是,一个个人物形象开始丰满起来,故事也变得有滋有味了;就这样,原先的一株小苗,在众人的精心培育下,渐渐地也就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一次和大陆的合作,无疑在我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吴总把在电影创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合作者们。我在《阙里人家》这部影片中,既不是编剧,也不是编辑,只是做了些上影文学部负责人之一该做的工作,他也在影片小结等好些场合提到过我。作为在场者,我得如实地说说这次经历。 自1984年1月,上海市政府任命老吴为上海电影局副局长后,至1992年他执导《阙里人家》的8年内,他只执导过3部影片:1984年的《流亡大学》是老厂长徐桑楚早就定下让他执导的。1986年的中外合拍片《少爷的磨难》在外方的一再坚持下,老吴只得担任总导演。1989年的《月随人归》,是由投资方全额投资点名要求他执导的。显然,执导《流亡大学》是老领导让新领导安心接班的慰抚,后两部是作为上影现任领导为上影生计而为。当然,想拍影片的强烈愿望从未在老吴心中低落过。但在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对影片的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有好的社会效果,又要产生经济效益,无疑,对一部影片的导演来说,压力越来越大。对既是名导,又是上海电影的主要领导的老吴来说,如要执导一部影片,其压力会更大。弄不好就会威信扫地。 然而1990年11月,老吴在山东曲阜参观了孔府、孔庙与孔林后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震撼,以及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生发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担当,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要拍摄《阙里人家》这样一部影片。在他心中大致有一个总体设想并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后,找我谈了一次话,详细地谈了他要创作这部影片的由来,介绍了矫健、周梅森、于艾平、杨江四位编剧的情况。最后,希望我以上影文学部副主任的身份与他们一起去曲阜下生活搞剧本。没有一点上级向下级下指令的做派,似乎在作为导演对剧本负责部门的“请求”。而我却早被他的“震撼”而震撼,被他的“社会担当”而敬佩,受他的抗压信心而感动,除了感谢他的信任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在曲阜,我们白天下生活,在各类实地找各色人物谈心采访。晚上,讨论剧本提纲,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顿饭走到哪吃到哪,一切从简。硬是从无到有,使剧本初具了规模。我知道老吴和四位编剧以及责任编辑,在剧本的创作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更明白有能力的创作者常会有极强的个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未瞎起劲地帮他们编剧本,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常从对剧本的要求上,提出不少质疑,充当了“对立面”的角色,有时弄得几位编剧很恼火。每每此时,老吴总是站在我的一边,他说:我们不能当鸵鸟,这些问题现在不提出来,以后还是有人会提出的。早提出早解决为好!这次创作,坚持了生活为创作之源,充分发扬了艺术民主,大家从生活出发,畅所欲言,提出各种方案和设想,从中挑选和凝练出最佳和最合理的,最后由老吴集中拍板。他由于艺术上功底深厚,又能听取大家的有益意见,他的归纳总结总让人心服口服,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曲阜,我与吴贻弓同住一屋,日夜相处在一起,除了创作上的事,他从未涉及到其他的话题。对创作中的争端,哪怕吵得脸红耳赤,事时事后总是对事不对人,从未对任何人背后说三道四过。以后,我们有机会相处在一处时,他也是如此,就是谈工作,谈艺术。这种正派的作风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阙里人家》这部影片的原始构思是老吴有感而发并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在剧本创作阶段,他又自始至终地参与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只要他开口,在编剧上署名,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据我所知,他自始至终都未曾有此想法。这种品质,大家都看在眼中。 我常会回忆起这次创作经历,虽在银幕上,我什么都不是,但一直使我难以忘怀,因为它是我平生最愉快的一次创作经历。我至今都衷心地感谢老吴给了我这次经历。
5、老吴的谢意
我在《人去影留》一书中,有一篇是写老上影的文学副厂长、文学部主任王林谷先生的。最后,有一段文字与老吴有关:“老王临终前问起上影的现任领导其实问的是吴贻弓,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又不便让我转告。此事,多年来我一直不敢向外提及,主要是怕有损老王的形象,似乎到了这地步还在在乎现任领导来不来看他。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在一次文联委员在外地学习期间,一天早上正好与吴贻弓一起吃早餐,就对他说了此事。吴贻弓听后久久没有说话,似乎深深地触动了什么。但他还是坦率地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他在执导影片《姐姐》时,是以受尽艰难的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风沙中继续勇敢地前进作为结尾的,寓意非常清楚:虽历尽磨难,前途未卜,但她们仍然不失理想,坚持前进……在送审时,时任副厂长的老王认为‘光明面’还表现不够,一定要打着红旗前进。虽然老吴认为这种表现太直露、公式化,但他也只能照此改动。影片公映后,确实有不少观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让老吴难以说清……我听后,恍然大悟,心灵顿时为之一震,老王啊,他在临走前,可能就为此事想对老吴说点什么……” 老王临终前说此话时,边上除了我外还有老上影的几位老同事,我把此事弄清了,如实地写出来,还了老王一个清白。虽我笔下谨慎小心,仍怕有损了老吴的形象。所以,我请老吴作序时,也想听听老吴的意见,此事可不可写?可写又如何表达为妥?老吴看完书稿后,没有提过任何一条意见或建议。却在他的序中写下了那么一段文字: “大陆在他的书稿前言中写道:‘铸成中国电影的辉煌,不是几个人的功劳,而是前赴后继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尽自身之力,添光加彩,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更值得大家怀念。’他在书中还这样写道:‘我想,倘若这一切什么都没发生,该有多好!发生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少受心中的煎熬。既然我已知道,我就应该把这些全都写出来。’‘我想,还会有好多人记着他,至少是我!’……是啊,世间情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执著更令人心动,又令人心痛的呢!这部书稿不仅使我重新置身于那隔膜已久的环境氛围之中,而且还使我回到了当年那些目日夜夜携手并肩的师长和兄弟姐妹们身边。所以,在这里,我要由衷地对大陆道一声谢谢!感谢他在上影建厂60周年的时候为我们送来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谁读到这段发自老吴内心的文字都会感动,尤其是我们老上影人。更尤其是我,因为我更能读懂这段文字的内涵。 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上海影协副主席、电影理论家石川教授在写老吴的传记里又提到了这件事:“两难的是,吴贻弓深深地明白,这绝非简单的创作观念之争,更清楚王林谷绝非刻意刁难自己,反之是为他着想,因为王林谷不仅是吴贻弓的领导,还是他的老前辈,更是一位资历丰富的创作者,代表作《舞台姐妹》可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至高水准,但被批判为‘大毒草’的政治厄运,成为笼罩在他生命中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他不会允许晚生后辈重蹈覆辙。”谁都可以看出,对此事所作的结论,是出自老吴之口、发自老吴之心的。 至此,我总算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我相信,如真有另一个世界的话,老王一定会拥抱着迎接老吴的,他们会倾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
6、在《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一书的首发仪式上
2018年11月26日下午,在老吴八十大寿的前几天,上海影协在即将卸任的主席张建亚的主持下,为石川教授所著的《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新书,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出席的大多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下一二代创作人员的代表人物,坐满了上海文联的大会议厅。 老吴当时在医院里检查身体,他是请了假出来的,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他和石川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大家的发言。这个新书首发式开得很特别,似乎没有人去顾及石川教授和他的著作,全在说他们心中的吴贻弓。是的,老吴的“传记”都写在我们的心中,世上没有一位作家能比我们更了解和理解他了。 我由于重病在身,基本上已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但这个会我一定要去的。我由于不善言谈,从未在大会小会上主动发过言,这次去,能见到老吴、听听大家说说他们心中的老吴,我也心满意足了。老吴由于肺癌开过刀后免疫力差,一直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也婉谢大家去他家探望,能见他一面也不容易。 我边听着大家抢着发言,边看石川教授的书。其实,这本写老吴的书写得还是较完整的,既有他的家庭生活和历尽的艰难,有着重写了他的艺术生涯,突出了他在任何情况下,“流年未肯付东流”。他随遇而安,但在艺术上从未停止过探索,除了执导的故事影片部部都有新意之外,他在美术片、话剧、音乐剧、电视剧等各种艺术样式中,只要给他机会,他都作过尝试和探索。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好能够做、可以做的事。”此话对我影响极大,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应该做好能够做、可以做的事。怨天怨地是无用的。老吴也如此,我们为何不如此呢? 当然,由于石川教授生晚了,无幸如我们那样能同老吴一起奋斗了几十年,所以,书中的观点尽管独具慧眼,但用有血有肉的材料来证实还少了些。如写老吴成家二十多年来一直住在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14平方米小屋内。我第一次与他相交就在这间小屋内,那时老吴刚当上局领导不久,因我的住处离他较近,厂领导让我在次日一早,老吴上班前,把一个剧本送往他家中,却让我撞见了令人窘迫的一幕:敲门进去,他正在斗室中收拾地铺。我进退两难,他却若无其事地笑道,家中小,住房一时还无法解决……然后又加了一句:“面包会有的!”对这前苏联一部名片中的这句名台词,我们都大笑起来,一下化解了尴尬的场面。石川教授如能把此类素材用上,或许会更生动些。 另外,书中对老吴当了领导后,为了繁荣创作,如何全心全意地为大家服务的情况,反映得也较少。这些,就我亲身感受到的就有许多:1987年,厂里突然通知我,让我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和张艺谋等一起,去香港参加电影节。接到这个通知,我愣住了!那时,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地工作。而作为编辑能有此机会与荣幸,这可是中国有电影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后来我才知道,是老吴点的名,他说,应该让这些同志去见见世面,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那时,我只是他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没有一点私交,更没有任何“猫腻”。此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后来所取得的成绩,是与他的鼓励以及对人事关系中光明面的信仰是分不开的。 后来,我作为中国电影界的代表,出访过法国、俄罗斯、日本、匈牙利、奥地利、摩洛哥等国,越走越远,却从未如那次去香港那样激动过。我唯一想说的一句话是:从1987年至今我所走过的路,没有让人可以在背后对吴贻弓1987年点名我去香港说三道四的。那次我从香港回来后,也没有去谢过老吴,我这个人比较传统,只是把这次机会看成是“组织”给的,只是更努力工作来报答“组织”罢了。而老吴也从未与我说及过此事,可对我的劳作仍然非常支持。20世纪90年代我参与创作的电影剧本《烛光里的微笑》《第一诱惑》等,都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才拍成了影片的。 直到老吴完全退下后,《烛光里的微笑》的导演吴天忍才约我一起去看了老吴一次,他和文蓉大姐还特意在饭店中请我们吃了一顿美餐。对此类事例,上影不少创作人员都有感受,如石川教授能采访到写上,此书当会更生动些。当然,最简易的办法是在石川教授采访老吴时能由他来说出。看来老吴对此仍然都未谈及,这越发令我敬重! 那天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拿了此书抢着去请老吴和石川签名留念。当老吴为我签书见到我时,说道:“你也来了?”我答曰:“我能不来吗?”他边为我签书,边关切地让我保重身体。 这天,老吴的情绪特别好,整整坚持了一个下午。谁都不会料到,十个月后,他却永远离开了他所深深地热爱着的这个群体……
7、老吴留下的一本书
以老吴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他文学上的造诣,在他退下来后是有好多东西可以写的,应该留下几本有价值的大书,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一本《花语墅笔记》,此书时以他居住的小区命名的,是他七十岁前的人生记录,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承蒙老吴的厚爱,此书出版后他即签送了我一本。 此书由《昨夜星辰》(专业札记)、《且听风吟》(序跋之类)、《一觚浊酒》(讲话和发言)、《闲情偶寄》(生活杂感)、《曾经沧海》(国内游记)、《地角天涯》(出访记)和《细雨梦回》(纪念文章)七辑组成。从老吴写下的这些“辑”名来看,就不难读出《巴山夜雨》《城南旧事》《月随人归》《阙里人家》这样的风格,而从内容上也确实写的都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他在书中又写下了那句话:“我们这代人只是做了些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为此,老吴在他古稀之年回顾往事时,虽然他曾辉煌过一个时代,却一点也没有自夸之意,那些都已成“昨夜星辰”“一觚浊酒”。在一次创作会议上,有人当面赞扬了他执导的《城南旧事》,并提出,现在怎么拍不出这样的片子了?老吴却在想另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城南旧事》是他在今天拍出的,观众能否像当年那样欢迎它、赞赏它?他曾深思再三,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观众的欣赏习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仍然孤芳自赏,那终究会被时代所淘汰。 但老吴绝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年代中“我们这代人只是做了些应该做、能够做的事”的同时,又十分尊重能“为中国做点事”的人。 老作家、老编剧沈寂,抗战时开始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港英当局无理驱逐。他从十多岁写到九十多岁,创作出了多部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却始终甘于寂寞,淡泊名利。老吴应邀为他的新作作序时,不但回顾了这位电影界、文学界前辈所取得的成就,而且着重赞扬了沈寂先生“为人处世一向低调,不事张扬”的长者风范和“虚怀若谷的品性”,并“对他老而弥坚的敬业精神肃然起敬”,文末,老吴恭敬地写下了“学生吴贻弓敬此,2007年5月18日”。 此书最后的《细雨梦回》一辑,收有老吴对亲友、师辈的14篇悼念文。他永远记着恩师吴永刚“叫我懂得要去追求人的心灵中最美的东西;叫我懂得要去追求银幕上最可贵的品格——质朴;叫我懂得要去追求一点点东西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就像他自己已经付出过的那样”。他永远记着老领导张骏祥先生的“要求别人很严格,要求自己更严格”。他在柯灵先生面前,只敢作为读者,“我不但从他的文章中学到作文的道理,而且也从他的文章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崇尚沈浮老厂长的忠厚仁爱、天真透明,让他认识到“天真对于艺术乃是不朽的生命”。他钦佩桑弧导演的“从不索取,只是默默耕耘”的“与世无争的贤者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此辑中的《小郝》一文,小郝是老吴当导演去北京送审片子时常为他开车的司机,也是他的影迷。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连家庭之间也常有往来,小郝的妻子出差来沪时,带了儿子就住在老吴家中,文蓉大姐热情接待,“亲切得像一家人”。他们的友谊延续了近三十年,不幸,小郝在53岁那年病故了。老吴满怀深情地写道:“我的经历中曾经有过许多像小郝那样的朋友,过去、现在,以至未来,都给了我无穷的关照,而我能给予他们的是少之又少。我真是幸运的。也许,过去,在小郝心里从来没有在意他曾帮了我什么,但是我知道,正是他过去对我的影片的直言,才给了我对后来影片有益的启示,尽管这些启示有时并非决定性的,但在我的认识积累中它们将延续到永久。”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趁活着的时候,都应从周遭的平凡人世中汲取养料,努力“为中国做事”。 我曾为老吴此书写过一篇书评,发表在《文汇报》的《笔会》上,题为《凡人笔记》。在我们人到晚年时,能不能也留下这样一部凡人笔记?
我总认为,老吴是该多留下几本书的。
8、与老吴的最后一面
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那天,我一早5时左右起床照例写作3个小时后也才8时多,不知怎的,我突然非常冲动地想去看望老吴。我给他夫人文蓉大姐打了电话,是保姆接的,说她还未起床。再问老吴起床了没有?说他在卫生间。他们俩都在,我就放心可去了。下楼时正好儿子回来拿样东西,他一听说我要去看老吴,便主动开车送我去,因为他也是老吴的影迷。 老吴和文蓉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能感受得到他们见我去是很高兴的。我说,自去年11月26日我们在老吴传记的首发式上见过一面后,一直想去看望他,但考虑到老吴八十大寿期间人来人往肯定较多,接着又是春节,所以拖至今。文蓉大姐因感冒没有出席那天的首发式,她问起了那时的情况,我便介绍起来……我突然有些疑惑地问她:老吴没告诉你?文蓉大姐说,他现在记性不好,明明刚吃过中饭,还要问她可以吃中饭了吗?我以为她在说笑话,但看看又不像。我望着老吴瘦得出奇的脸,心中真不是滋味。老吴却向我问起了老上影人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当然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不是这个走了,就是那个病了…… 我忙扯开话题,尽挑愉快的说。愉快的都在以前的创作中。我对他回忆了我们一起在曲阜边下生活边协助编剧创作《阙里人家》剧本的那些事,我们同住一间屋的那些日子。我说,这是我这辈子所参加的最难忘的一次创作活动……老吴微笑着说,他也这样认为。我非常可惜老吴在担任领导后没有机会再多拍几部好片子。老吴只是微笑着,没有其他反应。 文蓉大姐却忍不住说道,当时要老吴出任领导工作时,中央电影局局长方禹来做她的工作,她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当领导和愿当领导的人多得是,而像老吴这样的导演,从对社会贡献来说,还是让他当导演为好。方禹也直率地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谁当领导,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想当、愿当的人不在组织选拔的范围内,你再想、再愿也无用。选定了谁,作为党员都得服从。话讲到这份上,文蓉大姐只好无语。 老吴仍微笑着却把话题转到了他退休后所交的网友上。昨天,从江苏、浙江、上海等几个地方有12位网友结集前来看他,老吴饶有兴趣地把他们自编自制的网文集拿给我看,他说,他们都叫他的网名“申江小吴”,反叫他儿子天戈为“老吴”。他以仍然生活、融合在自己的观众之间为乐,而对昔日走来的一路经历,常以“记不起了”一言以蔽之…… 不知怎的,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思考《阙里人家》的内涵:这部片子,始终抓住了剧中父子的特殊冲突,对革命和传统、人性与亲情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反思,联系到当今社会的进步,这部在27年前拍成的影片确有其前瞻的魅力,且是永恒的。它在思想的开掘和艺术的探索上所取得的成绩,既是建立在老吴所执导的前几部影片的基础上,又远远作出了超越。历史会对这部经典影片作出更精确的解读。 次日——3月14日,一早,我迫不及待地把我思考的结果,打电话向老吴请教。我仍然感觉到他在电话那头的微笑,但他没有再说“记不起了”,而用“你说的都说到了我的心窝上……可惜这部影片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话回答了我。他可一直清醒着。我掉泪了。我感觉他那时的双眼也鼓满了泪水…… 6个月后——2019年9月14日清晨,老吴刚过完了中秋节后,“人随月归”也好,“月随人归”也罢,我虽有老吴的宅电和手机号码,再迫不及待,也与他难以通上一次话了……我写完此文时是2019年12月14日的清晨,几次的巧合,让我深信老吴会看到我这些蘸着泪水所写下的文字…… 老吴故后,悼念他的文字很多,我不会上网,只得恳求《上海采风》能否在老吴故世周年时能刊出此文,让我们共同来以此为祭。 本文经作者同意授权转载陆寿钧国家一级编剧
荐稿人:鈡 勤 2020-05-04 执行编辑:lxl 2020-05-07 责任编辑:ffy 2020-05-07 |
| 1 |
|
相关评论: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暂无相关信息
当前位置:首页